【时尚芭莎网讯】时尚芭莎
手砸下去的那个瞬间,王子川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手指和手掌的连接处,“感觉它凹进去一块儿”,他当即判断——“可能(骨)折了”。
而戏还在持续地演着,一句话接一句话,一个行动后面又是一个行动,偌大的剧场里未被光照亮的地方还有上千观众正在静静注视着台上发生的所有。时间一分一秒流动,他不能停下来。
这是突然发生在一出戏剧演出现场的事情,无法预设,不能重来,王子川是这出戏的男主角。
王子川在戏剧舞台上
直到事情发生过后N个小时后的深夜,看着自己的手被一层石膏又一层绑带又一层夹板箍成了一坨白色的馒头巨手,他才猛然惊醒:“啊?哥们儿手断了!”
次日,转战另外一个工作的拍摄现场,这只夸张的大馒头白手没处放没处藏的,那种“给所有人添了麻烦”的愧疚感于是乌云压顶一样将他淹没,这个人终于在无尽的“抱歉”里意识到了这一切“其实也没那么好玩儿……”但事已至此,也没有更好的招儿了,战斗欲几乎是没有的,“只能尽量想办法把这只手藏起来吧。”
之所以要几近详细地复述现实生活中发生在王子川身上的这桩事情与他跌宕起伏的精神状态,恰因为,这个真实世界里的他自己和他自编自导的电影长片处女作《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记者注:以下简称《朱同》)中的主角朱同小朋友,虽然不能说一模一样,但也基本上所差无几。
朱同十岁,属牛的王子川三十大几。
导演王子川
《朱同》给观者带来的种种内心震动,其中包含着各人对童年的回想、对逝去之物的遥望,还有最初的恐惧与期待。
那个在漫长的一天里忙忙叨叨滚一身泥,又跑又颠儿历险一样跌跌撞撞的小男孩,什么都不代表,又是任谁都可以在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些什么的。是什么?不必在此说。
在每个人都过得大差不差的相似童年里,是否又总归是那一点点最倒霉、最发怵、最不可告人、最和别人不一样的怪异,才构成了今天我们那一点点老能急中生智又一直敢选择狼狈的底气?是或不是,也不必在此说。
《朱同》杀青照
我们觉得颇可玩味与探究的一件事是,一个电影艺术工作者,是怎么做到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电影中将只属于自己的“童年往事”尽量淋漓地、无偏差地呈现于众的?王子川交付了什么,遗漏了什么?弥合了什么,又隐藏了什么?
以下是导演王子川的自述。
01
在戏剧演出的中间受伤这种事,第一时间,我心里确实会有点那种……叫什么?“好事之徒”。真的会挺高兴的,就觉得——“你看!又出事儿了!”
大学刚毕业我和几个朋友在上海做剧团,有一次临演出前搬家,我们丢了一万一千多块钱——钱装在一个大糖果盒子里,就是丢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钱是准备交给剧场做场租的。
丢完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高兴”,带着大伙儿就开始乐,就是觉得——怎么碰上这种事儿了呢?完了!我们的生活要完了!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感觉……它不是愁,是嗨。
以前还会遇到只有两天就演出了但戏才只排了一半的情况,熬一个大夜不睡觉排到天亮,早上回家的路上也是大伙儿一起哈哈大笑,又觉得“完了!这回是真完了!”好像每次一有“事儿”发生,就觉得生活给了你一个新的故事。
但每一次都没“完”。我们也没真的去解决什么,事情就是那么过去了——场租虽然丢了,戏还是照常演了;时间一到,没排出来东西也自然而然就都排出来了。
我在事情发生的第一刻会嬉皮笑脸,那不是别的,就是逃避啊。我就是一个完全不愿意面对“事儿”的人——小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让人欺负了,当时你看我啊,一点儿事都没有,甚至还会露出那种“嘿,儿子打老子了啊”的感觉。但是这个事就能留在我这儿,你明白吗?这个事其实根本没过去。我当时嘻嘻哈哈的,但是这个事带来的那个滞后的伤害——你跑不了,你也躲不开。
所以我并不希望“受伤”这种突发事故是所谓“创作必须存在的部分”,我希望创作必须有的部分是我突然发个财——这种不才是创作最好有的部分吗?都把自己弄骨折了,这是什么创作的必备组成?
是的,有可能,我是一个浑身上下都是弱点的人。朱同不是,我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就可以自我瓦解,他是无懈可击,我是风吹就倒。
有的观众看完《朱同》会特生气地问——你们这个电影怎么没有什么事件?你们到底要干吗?你到底想说个什么事?
这话我之前在First(青年影展)说过一次,我个人觉得创作对我而言真的就是一个发信号的过程:把你的童年经验、生长经历或者生命经验和你的审美趣味拼装成一个小发射器,然后你就发信号。
有人就能接收到你的信号或者有人跟你的信号同波段,就可以产生一种震动。这个信号不是有什么目的性的,就像光合作用——一个植物在那生长,有阳光照到它,它身边有二氧化碳,它就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再排氧气。
它不是有意识地排氧气,也不是为了让对面的奶牛把氧气吸进去再排二氧化碳回给我,然后奶牛挤奶的时候说不定奶水可以溅到我这根儿(小草)上,我才能蓬勃生长——完全没那么复杂。它啥也没想。
还有森林里的小动物,从小蛋壳刚孵出来就开始叫。别人问你为什么叫啊?你想表达什么?你都发出声音了,你肯定得表达点什么吧。你说它为什么叫呢?可能它就是饿了,也可能是它害怕,那就是一种本能,它就是要叫。
你说它叫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有同类来了,也可能有别的东西陪着他一起叫——然后听者会觉得诶,这个森林里还挺有层次的!一会儿有小鸟叫,一会儿有牛叫,还有树叶在动。但小鸟、牛、树叶主观上有那么多念头吗?也没。它就是一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叫就叫了。叫的结果还有可能是吸引来掠食者直接把它吃了呢。
确实,我凭着自己的本能做出的这些“发射”,是会给自己带来“被看透”的危险的,但作为创作者,你以为观众看不到你吗?都是会被看到的,你的审美和趣味会一览无余。
但是作品对我而言,就是个比喻,所有的内容可能都是你成长经历里的一部分,但当我打完这个比喻之后,它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作品跟你的生活本身中间还隔着一层东西,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恐惧感。
但如果你让我参加一综艺,就拍我跟我老婆天天24小时跟家呆着,或者你让我演王子川,那我真的羞耻,我受不了。
《朱同》杀青照
你说朱同跟我之间有多少连接?那肯定是有的,但在我看来,我不是一五一十地把我所有童年经历都写出来的。
《朱同》其实是个特别低姿态的作品,就像我以往的所有创作——包括舞台剧——我作品的姿态其实都很低,都是那种带着取悦式的、示好式的输出方式。
02
对,取悦的、示好的——我生活里对人也是这样。
每次见到陌生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示好,我就跟人家乐,就想告诉人家我是个没有攻击性的人,尽量再开开玩笑,让别人觉得我好像还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我的一种对外的沟通方式。
所以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担心过电影里朱同的行为会不会不讨喜,就是因为我所有的作品——从舞台剧到电影——都是一样的,我不会一上来就真的释放核心焦虑,或者我不会把核心焦虑摆在面上。
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买卖是卖糖豆,不是卖黄连——告诉别人我这个东西虽然苦,但吃了去火,不是。我现在住成都,经常可以在成都大街上听见有人敲“丁丁丁”,他就给你个小糖块,我觉得我就是卖糖的人。
那你说糖后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没有。我就是卖糖,你觉得有点儿不对劲,那八成儿是因为我手脏吧,做出的糖不是白的,是黑的,但是我没辙啊,这是个人卫生问题。做糖豆的后面是一个卖炭翁,伐薪烧炭,人间烟火色。
你想啊,他卖完碳不洗手就做糖——所以可以得出结论,《朱同》是一个“食品安全恐怖片”。诶对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卖炭翁卖完炭又搓糖,你知道有糖是拿手搓出来的吗?先拿锤子打,然后拿手搓……
对,示好。《朱同》这个片子,我个人觉得它也算是喜剧吧,至少我在持续地释放某种趣味。
我一直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有趣,我跟大家开个玩笑、逗逗闷子。我不是一个直接掏出来某种价值观,或者我拿着某一种观念的利器在这左砍右劈,我觉得我都没有,我就是在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趣味。
我没有任何能力告诉别人该怎么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面对生活呢,我只能分享一点生命经验,仅此而已。就是你在小蛋壳里叫,发现旁边也有一个人在叫,你发现这人也没得吃,甚至也快被掠食者吃掉了,大家相互慰藉一下吧。
整个片子的核心趣味——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一切,从2019年之后我开始动笔写这个故事到今天它被搬上银幕,都没有改变,而且是在一遍遍改的过程里让我越来越坚定它的结构和它真正意义上要承载的主题。
摄影/朱启凤
这里头就包括了《朱同》传达给你的所有感觉:“这电影到底讲啥了?”“这孩子到底怎么样了?”“这怎么感觉没发生什么事儿啊?”“这……就完了”所有类似这些感受,我觉得它都是我这个叙事审美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份锚定,可能这个片子就变成另外一个片子了。
在这件事上,我必须实打实地说一句,我感谢这个片子的监制饶晓志导演,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我没法说服任何人,但是饶晓志导演在这块给了我帮助。关于“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
最终他还是站在了我这边,他觉得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就要按自己最想拍的来拍,然后我也给他释放了一种感觉,就是您放心,我将来一定是能冲进春节档的、票房一两百亿的导演,咱们来日方长!
《朱同》杀青照
电影初剪剪出了一个140多分钟的版本,那时候我一个朋友看了还觉得特感动,那一版没有(最终上映)这个版本这么快节奏,也没这么多旁白,也没有现在这个甜——甜,味道的甜,现在这个甜度基本上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当时的所谓的“淡”也不是什么别的味道,只是一些感性上的感受不同。举个例子——我乱说的,具体准确的时间我记不住了——比如贺娜和朱同在教室里翻东西,现在我用了6分钟,一开始用了12分钟;还是他们两个人在水边,现在我用了3分钟,以前可能用了6分钟;还有大家一起除草那一场你记得吗,现在用了2分钟,以前留了5分钟。
可能原来的版本更奢侈一点,但现在这样也蛮好,也算是示好的一部分。
未来,不会有导剪版,不可能有。
我个人觉得,电影一旦定剪上映之后,就是它了,没有说“这东西以前是什么样,最后特可惜变成什么样”,绝对没有。我一直有个感觉,一样东西之所以是一样东西,只是我们了解它的时间顺序决定的,或者我们片面地认为这样东西它就在这,那只是我们认知的问题。
但实际上,也许是先有的这样东西,倒推出了这个创作者,倒推出了这个剧组,倒推出了电影最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全过程,倒推出整个创作者的童年——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就像朱同的命运一样,没有什么他能左右的,他就是在他的宿命轨迹上运动着而已,他以为他自己所有的动机也许都有点随机性,但你在一个绝对的时间线上看,他就是一个必然的轨迹。
这个片子也是,它就是这样一个98分钟的充满旁白的叫做《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电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就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喜欢它的任何一个部分,喜欢它的片名、喜欢它的旁白、喜欢它的时长——因为那就是所有跟这个电影有关的一切,或者说这些全部都是这电影的一部分,我都挺喜欢的。
03
一个小朋友在那儿做广播操,别人都在好好做,他在瞎抡,有个人从后头拍了他一下,然后他就以为自己被选中参加广播操比赛了,其实人家只是觉得“你干嘛呢?”打了他一下。
这就是最一开始,我下笔写的第一场戏。
在它之上有个名字叫《时代在召唤》——我是先想到了这个名字,然后想到这么一个情景,所以这个片子在我这儿其实一直就是个“时代在召唤”的故事:一个小孩被人从后头拍了一下,他就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好像“照见”了他。在我心里,这个片子就叫这个名字,当然后来我们又改了好几个名字,但在我看来,就都无所谓了。
哎哟,如果现在裹在一堆人里一起做广播体操,我当然不会像朱同那样乱抡乱打了,我尽量就可能假装自己很社恐,尽量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吧。尽量就跟大家做得一样,然后淹没在里头了,肯定的,如果真是做广播操的话。
我手里不存在一根什么与众不同的想要批判什么的小鞭子。
我反正一直都希望躲什么事都远点,我也不太愿意面对直接跟任何人或事发生任何冲突,跟什么都尽量有点距离感吧。因为直面某一种矛盾就会让那个矛盾显得很笃定。
比如恶,一旦你在叙事里给观众一个绝对的恶,那这个恶就得被解决,要不然你的姿态是什么?我是特别害怕立场变得特别清晰,那种清晰会让我特别不安和焦虑。
因为你一旦树立一个特别普世的“恶”的出现,必须就得有一个价值观式的东西冲进来,最后到底是善良战胜了邪恶还是邪恶战胜了善良?就变成一个非常无趣的情境或者无趣的局面,那个对我来说特别让我想远离。
我真的打小儿就不喜欢玩“拳皇”,我一看到它出现在这种用电视玩的游戏机上就感觉要惹麻烦了。我对有对抗性和竞争性的东西真的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也不喜欢打篮球,特烦别人撞我。
竞技类的体育项目,我能接受的极限也就是……乒乓球吧,咱俩至少隔个台子,就别奔着脸互相抽,可以往球案子上抽。
所以片子接近结尾的地方,朱同在学校边缘的草丛里把男同学打倒那一幕,我不想给一个结论说那是他的想象还是真实的发生,哪一种回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无趣的答案。那个东西的趣味是在于,它是一个模仿和反射,它不提供什么价值观,也不宣布这个行为的对错。
人不就是这样吗?模仿——不就是大伙儿每天在干的事吗?不只是未成年阶段,成年人不也每天在模仿他们身边的所有人事物吗?大家都在模仿着彼此的所有、一切,这里边有什么评判吗?“善恶”“道德”这些概念不也都是在这些被模仿的行为里产生的吗?
并不是说大家一上来有一个主观程序——这个程序就叫“道德安卓2.5”“道德加强版3.0”“道德4.6.17”……也不是吧。这个过程中,大家的标准也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还挺慢的,就是一个群体互相模仿的过程。
哎你想过吗,今天一堆人坐在这说“咱是一代人”,你说大伙儿怎么说出这句话的?或者有的时候动不动就说“你瞧人那边,你瞧咱这边”,这天儿是怎么聊的呢?在区分“人那边”和“咱这边”的时候是用什么来分的?我现在明白了,是“烙印”,就是那些你逃不了的,打进你骨头里的东西——不是表面的伤疤啊,那个无所谓的,现在祛疤的招儿这么多。
真正的烙印就是:你就是这么想的,你这辈子遇到事你只能这么想,而且至少第一时间你只会这么想,最终你可能选择不这么做,或者你换了几种做的方式,但是你第一时间遇到某一件事情,第一反应一定是这个。这个烙印是什么?没法儿说,一说出口就容易错。
最猛的东西是你看不见的“什么”。
04
《朱同》里,龙里实验小学教学楼上那几个标语,是我们看景的时候从另外一个拆掉了的学校墙上直接拿过来的,“未来”“自强”——这几个字多好啊。
我,小,时,候,相,信,未,来,吗?
我……我相信吧……小时候……我……期待未来吧,嗯,我不相信,关键是我相信什么呢?蜘蛛网也没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啊……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未来什么,但我总期待着未来。包括到今天,我都期待未来。
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我没法活在当下,我不是活在对过去的焦虑里就是活在对未来的幻想里。所以我到今天也是持续地期待未来,期待有个更好的未来。
至于“自强”,哎呀,自强真的能激励到一个人吗?这可能得分人吧,而且你不说我也没仔细想过,什么叫“自强”?自洽是不是好一点?对,我应该给教学楼墙上换个标语——“当下”“自洽”,而不是“未来”“自强”,对吗!
对,你发现了,终剪里有一个细节,演贺娜的小女孩有一场说错了一句词,我把那一条剪进来了。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有趣,就像电影的文本一样,你对表演审美的输出也是一部电影审美输出的一部分,这个说错词了,可能就是我个人认为表演里比较有趣的地方。
我不是接受不了完美无瑕,我只是想问,怎么算完美无瑕呢?
真实的东西不可能无瑕吧?怎么可能无瑕?也许是我没见过什么太无暇的东西,我觉得唯一的无暇就是真实,可能真实这个事本身无暇,但是真实里全是瑕。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王子川有什么超能力是现在还没失去的吗?
有!就是接受采访。真的,小时候我就老幻想自己接受采访,我就会一个人在那说话。我长大了也这样,别人永远不知道我在嘟囔什么,其实我在接受采访,我在问我自己问题。“你刚刚为什么急了?”“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急了?”或者“你刚才为什么不生气?”“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兹要有个事儿出来就问自己,采访我自己——为什么?我就感觉我自己是个大明星,有一个记者真的追着问我,我也真的想通过回答问题把这个事弄明白,而不是说只是让这个记者问我一个我真的知道答案的问题。我采访自己的问题都是我也不知道答案的。
你说朱同这一天天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哪一个都是劈头盖脸的“天都快塌了”,他是怎么做到一样一样度过的呢?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不用度过,因为你度不度,过不过,生活还在继续。
你不需要“过”,有的时候磨难是一个状态,它不是“过去”或者“过不去”的事儿,它可能是某一种情绪或者某一种你面对外部世界给你回馈的方式。有的人它就是这么在生活,就跟那个东西一直相处,或者他在里头逗闷子,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八个字:当下,自洽,未来,自强!
好的,口号喊完了。之后是什么呢?谁知道呢?
监制/葛海晨
编辑/Timmy
采访&撰文/吕彦妮
排版/王路
©版权声明:时尚芭莎网编辑时尚芭莎,本文系时尚芭莎网独家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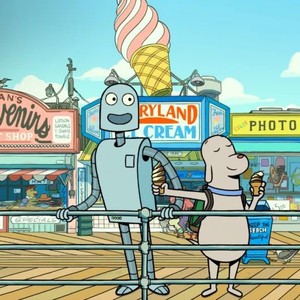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48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483号
